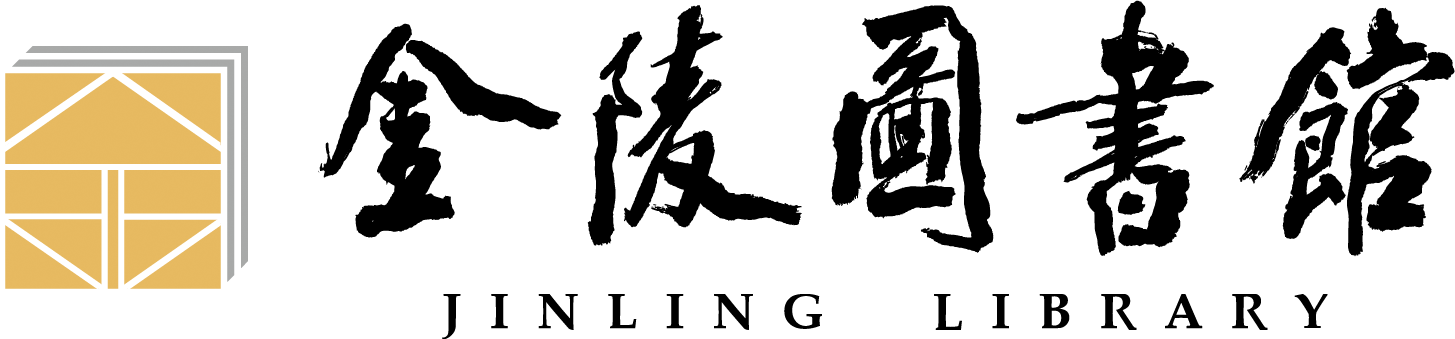![期刊架位号[5106] 期刊架位号[5106]](./W020250321521185614819.png)
晋成帝时,虽然重新规划建设了建康都城,但由于东晋政权的流寓性质,长时间内没有放弃恢复中原的宏伟大志,因此终东晋之世,建康城虽有过三次修缮,但都城的规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双阙、明堂、南北郊坛等重要礼制建筑也没有建成或完善,甚至都城城墙都是由竹篱围成,城门也是竹木结构,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宏伟。
然而,进入南朝以后,尤其是在刘宋孝武帝时期,建康都城的改制措施频繁出现,各种礼制建筑及观念上的外郭空间最终形成。
作为中国南方政权的都城,必定会为周边国家的使臣建立 “客馆”。倭国使臣来到建康后,住宿及各种外交礼仪活动也应该在 “客馆” 中进行。
东晋时期的客馆,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九载,“宣阳门内过东即客馆省、右尚方,并在今县东一里二百步”。王志高《六朝建康城客馆考》认为 “客馆省” 作为街署是不存在的,并依据《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中的片言只语认为,主持来使的部门客省或典客省位于宫苑之内。因此,《建康实录》所言都城宣阳门内的 “客馆省” 或为 “客馆” 之误。王文论述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是指出 “门客省” 或 “典客省” 位于宫苑之内;二是《建康实录》所言 “客馆省” 或为 “客馆” 之误。前一点尚缺乏依据,后一点关于东晋客馆的位置基本可信。
其实,历代版本及当下通行的两种点校本《建康实录》的上引文句是有讹误的。笔者在指导 “《建康实录》读书班” 时,依据基于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复原的东晋建康城示意图,对上引《建康实录》文句作了修订,认为当作:“宣阳门内道西即客馆省、右尚方、并在今县东一里二百步。” 如此,东晋客馆则位于都城正门宣阳门内御道西侧。这个地点,与后世隋唐长安城皇城正门朱雀门内道西的鸿胪馆一致。东晋义熙九年 (413 年) 到达建康的倭国使臣应该在这一带活动。
进入南朝以后,随着外交活动的频繁,客馆的数量、位置有了很大变化。宋建国后,在建康设立南、北二客馆。南、北二客馆并非因其所在位置命名,其中的 “北客馆” 是北朝来使专用的客馆,其他国家的来使均使用南客馆。北客馆又称 “行人馆”,据考证位于建康城外郭 “娄湖篱门外”,以示有别于诸夷。
南客馆的位置,在倭国使臣频繁往来的南朝刘宋及后续的齐、梁、陈时期,没有资料显示有过变动,推测应该与东晋时期一致。仍然位于都城宣阳门内道西。如果这一推断不误,那么,东晋成帝时期规划建设的建康城客馆,其所处位置影响到了隋唐长安城鸿胪客馆的设置,这是南朝制度影响隋唐的一个例证。建康城将接待北朝来使的 “北馆” 或 “行人馆” 设定在观念中的外郭篱门之外,这是否也影响到了北魏洛阳城在郭外设置 “四夷馆” 和 “四夷里” 的做法,同样值得关注。
自东晋义熙九年倭国第一次来使,到刘宋昇明二年最后一次来使,六十余年间的约 11 次来使,他们的住所及主要的外交礼仪活动,均在宣阳门内道西的客馆。
宣阳门,长达七里的御道穿门而过,往南通向都城南端的朱雀门,往北正对宫城正门大司马门;门内御道两侧集中了中央衙署,门外御道东侧是太庙,西侧是太社。这里是整个东晋、南朝建康城礼仪空间的核心地区。
宣阳门又称 “白门”,“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皆绣桶藻井”。给人一种高大坚固的印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前文已言及,在东晋与南朝刘宋这长达 150 年的时间内,包括宣阳门在内的建康都城六门及门上的重楼可能都是用木桩与竹篱这类简单易得的建材构筑而成的,而城门之间所谓的都墙,亦全由竹篱围成。萧齐建国后的建元二年(480 年)十月,都城墙才逐渐改造成夯土包砖墙。这是倭国使臣未能看到的风景。
南朝进入萧梁时期,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客馆的数量及位置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客馆的数量上,出现了 “六馆” 之说:一曰显仁馆,处高句丽使;二曰集雅馆,处百济使;三曰显信馆,处吐谷浑使;四曰来远馆,处蠕蠕(柔然)使;五曰职方馆,处干陀利使;六曰行人馆,处北朝使。除北朝使专用的行人馆依然位于娄湖篱门外,其他五馆被集中安置在都城东侧的青溪以东。这一带临水傍湖,青山远眺,风景优美。但由于萧梁时期倭国再未遣使建康,因此无缘目睹诸馆林立、层楼迭起的景象。
(《环球人文地理》2025年1期 [5106])